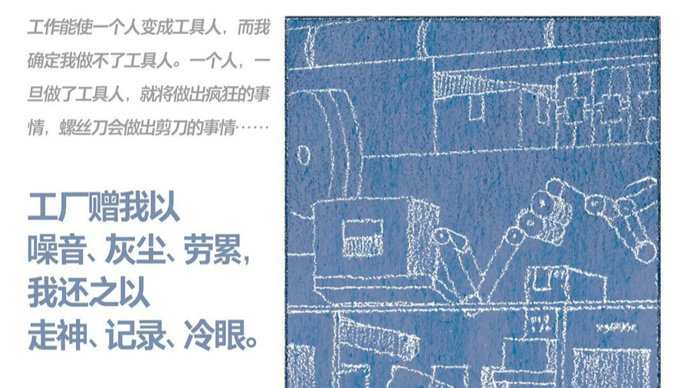如此工作二十年,他不甘做一个沉默的螺丝钉和工具人
来源网站:news.qq.com
作者:上观新闻
主题分类:劳动者处境
内容类型: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
关键词:打工人, 工厂, 生活, 父亲, 故事, 工具
涉及行业:制造业, 纺织/服饰/家具
涉及职业:蓝领受雇者
地点: 江苏省
相关议题:无
- 张赛在工厂打工二十年,期间不断记录和反思工人的真实生活与精神状态,表达了工人个体的呼吸与呐喊。
- 他通过写作关注身边工友的生存处境,试图用采访等方式让更多工人的声音被看见和听见。
- 张赛质疑工厂的考核制度,关注其中的暗箱操作和非人性化部分,展现了工人对工作环境的思考与抵抗。
- 他认为工厂生活容易让人变成“工具人”,但自己坚持独立思考和精神追求,不甘于沉默和麻木。
- 张赛的写作为普通工人群体留下了珍贵的记录,让更多人看到工人个体的存在和他们的真实故事。
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,仅供参考,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。
2010年7月,高考刚结束一个月,因母亲生病住院,父亲需回家安排手术事宜,但工厂的机器不能停止运转,我便主动为父亲顶班。那是南通的一家纺织厂,需要的是纯粹的体力劳动,我才干了一周活就叫苦不迭(我无法使用“工作”这个词,在我们老家,“工作”就是坐办公室里吹空调的,而出力气的只能称为“干活”),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我至今还记得,在一家小超市跟父亲打电话时,眼泪一直掉,不是因为感到辛苦,而是想到父亲以后还要一直干这样繁重的体力活而感到难过。我哽咽着跟父亲说,换个工厂,以后再也不干这样的活了。可是,从2006年到2025年,虽然纺织厂换了几个,可父亲几乎都是在干同样的活,而他在这样的工厂已经打了近二十年的工。当然,这还不算之前打过的其他工,比如去山西挖煤、去天津拔钉、去北京搞建筑。
张赛大我几岁,我们算是同龄。张赛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大概也同龄,而且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的初代打工人,张赛说他“如此打工二十年”,而我们的父亲,毫不夸张地说,已经是“如此打工四十年”了。这也是我读他这本《在工厂梦不到工厂》会有如此深刻共情的原因。哪怕我现在成了一个“坐”办公室的,因为我的经历、我父母的经历、我身边亲友的经历,我依然会被张赛的文字打动,准确地说,是被他传达的情绪、内心的声音所感染。
张赛
一个“不合群”的人
回到这本书,这是张赛的第一本书,记录了他在泉州一家卫生巾厂打工时的见闻与思考,并由此串联起他20年的打工生涯:当过保安、跑过快递、送过外卖……从书中可以得知,张赛话不多,是工友和孩子眼中的“书呆子”,这让我想起了“打工诗人”许立志的一首名为《冲突》的诗——“他们都说/我是个话很少的孩子/对此我并不否认/实际上/我说与不说/都会跟这个社会/发生冲突。”张赛的这本书未尝不是他与社会、与工厂、与打工“冲突”的产物。他有太多的故事和感悟,这些文章是他对打工经历的真实记录,从中可以看出一颗螺丝钉的呼吸与呐喊,就像他在序言中所说的:“我关心个体,关心工人,因为我是个体,我是工人,我关心我自己。”
前段时间来自河南濮阳的“爱读书的工地大叔”刘诗利因为喜欢读书而爆火,比他喜欢读书的人多的是,为什么唯独他能够感动那么多人呢?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反差感。一个常年在工地打工的农民,栖风宿雨,饱经沧桑,似乎与阅读这种“高雅”的趣味风马牛不相及,可他却放不下书本,经常在忙碌的空隙躲进文字的海洋。无疑,他是一个“不合群”的人。
和他的老乡刘诗利一样,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张赛也是一个酷爱读书的“不合群”的人。虽然初中就辍了学,但他对阅读的热爱始终如一。他说:“我不喜欢说话,不喜欢出去玩,每天看书,每天写日记,每天搞创作。”身为一个常年为生计奔忙的打工人,书籍是他最好的伙伴,也是他抵抗庸常生活最有力的武器。他打工往返的行李箱中,有一半是沉甸甸的书。休闲时,工友们要么躺在宿舍睡觉聊天,要么结伴出去玩乐,只有他一头扎进当地的图书馆,享受独属于自己的那份隐秘的快乐。他还说他在工厂找不到志同道合的女朋友,喧嚣的工厂怎能“容下”一张安静的书桌和一个手不释卷的灵魂呢?
张赛是打工人中的“异类”,不仅因为他喜欢读书,还因为他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工厂“禁止思考,禁止难受,禁止快乐,禁止白日梦”,可他不甘做一个沉默的螺丝钉和工具人,而是要成为一根会思考的芦苇。他没有被工厂的规章制度所规训,也没有因柴米油盐的日常而麻木,他保持着对工厂和工人的观察与思索,如他所写:“那时候已经意识到工作能使一个人变成工具人,而我确定做不了工具人。一个人,一旦做了工具人,就将做出疯狂的事情,橡皮擦会做出硫酸的事情,指挥棒会做出大铁锤的事情。”比如,针对工厂考核制度,张赛会质疑考核分打分的依据,其中有哪些暗箱操作,又存在哪些非人性化的部分;再比如,面对乏味、重复的工厂生活,他化身为“福尔摩斯”,调查食堂桌子上两瓶未开封的绿茶是谁的?茶水间的毛巾又是谁的?这些行为看似无意义,实则是他用这种方式去解构枯燥的工作、消解单一的生活。
“总要有人看见尘埃里的杯子吧”
张赛不仅仅是阅读、写作和思考,他还在行动,去关注身边一个个微渺的个体。或者说,他“把自己作为方法”,认真观察“附近”的人(工友)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。在书中,他不只是在写自己,还是在写许许多多个“我”:老盐、白公子、小树、老甘、萌宝……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,来到同一个工厂。在这种群像的描写中,张赛还原出了工厂中的众生相,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普通工人曾穿越过怎样的生活风暴。
如在“卫生巾厂狂想曲”中,张赛通过叙述自身的打工生活,勾连出了工厂其他工人的故事,哪怕他们只是流水线的一部分,每个人依然拥有一部自洽自足的编年史,包括他们的成长、家庭、情感、生活等等。而在“一个工人决定去做更多”中,他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身边的工人们,决定以采访的形式挖掘出工友们不被人关注的人生,用他本人的话来讲,“我不想只做一个旁观者,我想采访他们,进入他们的视角,听他们讲自己的打工故事”。遗憾的是,这是张赛又一个“书呆子”式的想法,他怀着满腔的理想主义去记录活生生的现实,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,最终只有石头、阿飞、韩珮三人接受采访,无法支撑他原先设想的一本书的体量,似乎这是一个失败的计划。
但在我看来,张赛并没有失败。当他产生这种想法并付诸行动的时候,他就已经成功了。往大了讲,中国几十年的崛起,作出贡献的不仅仅是科技、教育、金融、互联网等“高大上”行业的精英,还有无数渺小的工人默默地托举,而后者的声音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张赛既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,也是在为成千上万个老甘、石头、阿飞代言:他们没有“回家自由”,与家人和孩子团聚的周期以年为单位;他们并非外人眼中的“千人一面”——“顺从、听话、吃苦、耐劳、没有理想”,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“无声反抗、无声生活”。
张赛的行动,让我想起了罗新教授的著作《漫长的余生》中的一段话:“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,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,没有他们,历史就是不完整、不真切的。我们还应该看到,对普通人的遮蔽或无视,是传统历史学系统性缺陷的一部分。”而当下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,这些工人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主体,张赛书写这些工人的故事,也是为当下与历史留下一份宝贵的备忘录,就像他为茶水间的水杯拍下照片——“总要有人看见尘埃里的杯子吧。总要有人记住尘埃里的杯子吧”。
近几年来,像张赛这样的草根写作者接连涌现,并被称为“素人写作”,同时被纳入“新大众文艺”的范畴。比如胡安焉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、王计兵的《赶时间的人》、范雨素的《久别重逢》等。我很喜欢这样的书写,尽管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,却拥有丰富多样的生命经历,储备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。当他们将这些故事落地为文字,或许没有华丽的文风,但充满着真实生活的气息和野生野长的糙砺感,足够朴实有力,自有一番感动人心的力量。
就像《在工厂梦不到工厂》,单论文笔并不是很突出,但它胜在朴素、鲜活、地道。张赛没有描摹诗意生活,也没有歌颂苦难,而是真诚坦率且不乏幽默地书写自我,而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呐喊、一种反抗、一种升华。
尽管学历不高、四处奔波,但张赛的写作却体现出他丰厚的精神生活,是一种对“读书无用论”的反驳,也是对庸常生活的反抗。进一步讲,作家并非一种“特权”,很多出身底层的人,依然可以拿起笔来,写下或诚挚动人或幽默诙谐或质朴无华的故事,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在场。他们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